作者:余荷
ARDS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可能也是导致前期很多ARDS研究获得阴性结果的原因,并且这种异质性也导致了治疗结果的差异。ARDS可以按照临床进行分型,也可以进行生物学分型。临床分型包括:根据柏林定义的轻、中、重度分型,肺内源性和肺外源性分型,以及影像学的局灶性和非局灶性分型。在生物学分型方面,上皮损伤和内皮损伤有多种生物标志物,但目前主要着重于ARDS的预测和预后的判断等方面,这些标志物真正用于治疗中非常少。对于全身炎症反应,目前也有较多的生物标志物可以用于ARDS分型。此外,肺泡反应也可用于分型,但其主要取决于肺泡灌洗液、灌洗部位、可能的炎症反应等。目前在生物学分型中使用最多的是血中的生物标志物。
2014年发表在Lancet Respir Med 杂志的一项研究拉开了ARDS生物学分型的帷幕。该研究利用两项大型ARDS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数据(ARMA和ALVEOLI研究)共1022例患者,根据炎症表达水平分为低炎症型(Phenotype 1)和高炎症型(Phenotype 2)。与低炎症型ARDS相比,高炎症型ARDS的血浆炎性生物标志物浓度更高(IL-6、IL-8、TNFR-1、PAI-1均升高,蛋白C降低),更易合并休克和代谢性酸中毒。该研究将生物标志物与临床指标相结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生物学分型的ARDS患者预后不同,与低炎症型相比,高炎症型的病死率更高,无机械通气时间更短,器官功能不全的时间更长。整体而言,高炎症型ARDS患者的预后更差。2017年发表在Thorax杂志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对ARDS患者外周血反应炎症、凝血与内皮活化的20个生物标志物的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该研究仅采用了生物标志物,没有结合临床指标。研究将患者分为“uninflamed”和“reactive”两型,reactive型患者的病死率明显升高。研究中提及了4种生物标志物能够准确预测ARDS分型,分别是:白介素-6(IL-6)、γ干扰素(IFN-γ)、血管生成素(Ang)-1/2、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1(PAI-1),并且它们分型的曲线下面积较好。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生物学分型的基因表达存在差异。对“uninflamed”和“reactive”两种类型ARDS患者的白细胞mRNA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3的基因表达不同;reactive型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活化和氧化磷酸化相关基因表达上调,uninflamed型患者的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途径上调。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通过汇总分析5项RCT研究、2项队列研究以及1项儿科队列研究,也证实了不同生物学分型的ARDS患者预后不同。所以,生物学分型在评估ARDS预后和预测不良结局方面对临床有一定的帮助。有学者对生物学分型的稳定性也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对ARDS中两项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在两个队列中,在第0天分组为低炎症型的患者在第3天仍有93%为低炎症型,分组为高炎症型的患者在第3天也有91%停留在高炎症型。从下图中也可以发现,无论在第0天还是第3天,生物学分型都是较为稳定的。这也有利于我们识别高炎症型患者对某些治疗的反应。
图源:Thorax, 2018, 73(5):439-445.
生物学分型被提出不久,当时就有研究显示不同生物学亚型对PEEP的反应存在差异。高炎症型ARDS患者采用高PEEP策略,90天死亡率降低,无机械通气时间、无器官功能衰竭时间均延长;低炎症型ARDS患者采用高PEEP策略,90天死亡率增加。所以,高炎症型患者更适合高PEEP策略,低炎症型患者更适合低PEEP策略。针对FACTT研究(1000例患者)的二次分析发现,对于高炎症型患者,如果采用保守性液体治疗,60天和90天病死率都高于开放性液体治疗;而对于低炎症型患者,如果采用开放性液体治疗,病死率会更高。所以,不同生物学亚型的ARDS患者对不同液体策略的反应也不同。高炎症型患者更适合积极的液体复苏,而低炎症型ARDS患者则需要采取相对保守的液体复苏策略。关键是我们如何区分这两种亚型。这项研究也对生物标志物识别亚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采用了3个生物标志物—IL-8、TNFR-1、碳酸氢盐,它们能很好地识别生物学亚型,后续还增加了2个变量,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和分钟通气量,但增加的这两个变量并没有增强对生物学亚型的识别能力。他汀类药物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在ARDS的治疗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HARP-2研究最初得出了阴性结果,但对该研究的二次分析发现,在高炎症型ARDS患者中,与安慰剂比较,使用辛伐他汀治疗能够降低病死率,并且能够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在低炎症型ARDS患者中并未发现他汀类药物有治疗获益。该研究的分型采用临床数据集和生物标志物(IL-6,sTNFR-1,肌酐,血小板),这些肺外指标可能更有利于进行分型,而氧合指数、平台压等并不适合作为分型指标。另外,对SAILS研究(745例患者)的二次分析发现,在ARDS不同生物学亚型中未观察到瑞舒伐他汀的治疗效果。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瑞舒伐他汀与辛伐他汀的药物共性不同,辛伐他汀具有亲脂性,而瑞舒伐他汀则具有亲水性,可能导致了这两种药物在抗炎方面的差异。既往关于他汀类药物治疗ARDS,仍以辛伐他汀居多,瑞舒伐他汀相对较少。4. COVID-19相关ARDS不同生物学亚型对激素的反应有研究探讨了不同亚型COVID-19相关ARDS(CARDS)对治疗的反应,研究采取了潜在类别聚类分析方法,将ARDS患者分为1级和2级,结果发现2级与高炎症型基本相似,炎症反应指标更高,具有较高的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率,预后更差;86%的CARDS 1级患者被归为低炎症亚型,81%的CARDS 2级患者被归为高炎症亚型。进一步分析发现CARDS不同生物学亚型对激素的反应也不同,炎症反应高的患者使用激素治疗,90天死亡率更低;炎症反应低的患者使用激素治疗,90天死亡率没有显著变化。区分生物学亚型能够帮助我们识别有治疗反应的患者。2021年针对IL-6受体抑制剂——托珠单抗的研究得出了阳性结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纳入了炎症反应比较高的患者。除了低氧(氧饱和度<92%)这一指标,研究还通过C反应蛋白(CRP)来判断炎症反应,研究中CRP≥75 mg/L的患者确实获得了阳性结果。2024年新发表的一项研究探索了生物学分型在肌松剂使用中的价值,然而并未发现肌松剂治疗对不同生物学类型的预后有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炎症表型中高表达的基因与先天免疫反应、组织重塑和锌代谢有关,低炎症表型中高表达的基因与血管稳定性、抗炎细胞因子转运蛋白和细胞存活相关。在高炎症表型中基因富集通路:第0天,细胞周期和死亡、代谢和生物能量衰竭以及真核起始因子2(EIF2)途径;第2天,胶原合成分解以及中性粒细胞脱颗粒途径。在低炎症表型中基因富集通路:第0天,PD-1和IFN信号通络,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合成通路;第2天,PD-1和IFN信号通络。所以,不同的生物学亚型,基因表达的差异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血浆中检测出的蛋白质与MRA表达的相关性很差,这可能涉及蛋白转录等多种原因。从该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肌松剂能够避免ARDS患者人机不同步和自主呼吸诱导的肺损伤等,其炎症调节作用非常小。所以我们在识别出生物学高炎症亚型时,如果采取了并不作用于该途径的治疗方式,大概率会得到阴性结果。既往多项RCT研究提供了多种生物标志物,包括IL-6、IL-8、PAI-1、INF-γ、sTNFR-1等,有没有更简单的生物标志物识别方法?有研究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NHLBI ARDS网络中的3个队列(ARMA, ALVEOLI, FACTT)共2200例患者,以选择6个最重要的分类变量(包括IL-6、IL-8、碳酸氢盐、蛋白C、sTNFR-1、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用于开发嵌套逻辑回归模型。然后在验证队列中评估预测精度最高的逻辑回归模型(SAILS; N=715)。结果发现IL-8、碳酸氢盐、蛋白C能够很好地识别这一模型,并且也得到了验证。另外一个验证队列发现,IL-6、sTNFR-1和血管活性药物也能够比较好地识别不同的生物学亚型。简约模型除了识别生物学亚型,还能发现对辛伐他汀的治疗反应。也有研究使用临床指标进行机器学习, 也能够很好地识别生物学亚型, 并且机器学习的临床分类模型也能很好地识别生物学亚型及对液体策略和PEEP的治疗反应, 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022年发表的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
2023年发表了一项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的事后分析,纳入了41例接受经鼻高流量氧疗(HFNO)的ARDS患者,24小时内测得生物标志物—RAGE、SP-D、Ang-2、IL-6、IL-8、IL-33和sST2,结合这些生物标志物进行聚类分析最终得到两种生物学亚型;在患者基线情况类似的情况下,这两种生物学亚型的结局和转归仍然不同,高炎症亚型机械通气时间更长,插管概率更高,ICU住院时间更长,预后更差。所以在非插管ARDS患者中,通过生物标志物来识别ARDS亚型同样适用。
临床迫切需要获得一个能够在床旁快速识别ARDS生物学分型的指标。目前正在进行的PHIND研究值得期待,该研究在床旁快速分析血浆IL-6和可溶性TNFR-1水平,来识别ARDS的生物学亚型。
ARDS的生物学异质性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尽管大多为二次分析,但在很多前瞻性队列中也得到了验证。识别ARDS的生物学亚型有助于推进特异性治疗,且主要集中在炎症反应调节方面,血浆生物标志物对ARDS生物学亚型的预测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尚需解决的问题有:床边早期区分亚表型的可靠生物标志物,生物学亚型是否ARDS特有,潜在的生物学驱动因素,血浆以外的生物标志物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问题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1] Bos LDJ, Laffey JG, Ware LB, et al. Towards a biological definition of ARDS: are treatable traits the solution?[J]. Intensive Care Med Exp, 2022, 10(1):8. [2] Calfee CS, Delucchi K, Parsons PE, et al. Subphenotypes i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data from two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Lancet Respir Med, 2014, 2(8):611-620. [3] Bos LD, Schouten LR, van Vught LA,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distinct biological phenotyp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by cluster analysis[J]. Thorax, 2017, 72(10):876-883. [4] Bos LDJ, Scicluna BP, Ong DSY, et al. Understanding Heterogeneity in Biologic Phenotypes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by Leukocyte Expression Profiles[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9, 200(1):42-50. [5] Wick KD, Aggarwal NR, Curley MAQ, et al.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d clinical trial designs i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 Lancet Respir Med, 2022, 10(9):916-924. [6] Delucchi K, Famous KR, Ware LB, et al. Stability of ARDS subphenotypes over time in two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Thorax, 2018, 73(5):439-445.[7] Famous KR, Delucchi K, Ware LB, et al.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Subphenotyp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Randomized Fluid Management Strategy[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7, 195(3):331-338.[8] Calfee CS, Delucchi KL, Sinha P, et al.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subphenotypes and differential response to simvastatin: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Respir Med, 2018, 6(9):691-698.[9] Sinha P, Delucchi KL, Thompson BT, et al.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ARDS subphenotypes: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statins for acutely injured lungs from sepsis (SAILS) study[J]. Intensive Care Med, 2018, 44(11):1859-1869. [10] Sinha P, Furfaro D, Cummings MJ, et al. Latent Class Analysis Reveals COVID-19-relate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Subgroups with Differential Responses to Corticosteroids[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1, 204(11):1274-1285. [11] RECOVERY Collaborative Group. Tocilizumab in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 with COVID-19 (RECOVERY):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open-label, platform trial[J]. Lancet, 2021, 397(10285):1637-1645. [12] Sinha P, Neyton L, Sarma A, et al. Molecular Phenotypes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the ROSE Trial Have Differential Outcomes and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That Differ at Baseline and Longitudinally over Time[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4, 209(7):816-828. [13] Serra AL, Meyer NJ, Beitler JR. Treatment Mechanism and Inflammatory Subphenotyping i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4, 209(7):774-776. [14] Wu L, Lei Q, Gao Z,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Phenotypic Classification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 Narrative Review[J]. Int J Gen Med, 2022, 15:8767-8774.[15] Sinha P, Delucchi KL, McAuley DF,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parsimonious algorithms to classify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phenotypes: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Lancet Respir Med, 2020, 8(3):247-257.[16] Sinha P, Churpek MM, Calfee CS.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er Models Can Identify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Phenotypes Using Readily Available Clinical Data[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0, 202(7):996-1004. [17] Maddali MV, Churpek M, Pham T, et al. Validation and utility of ARDS subphenotypes identified by machine-learning models using clinical data: an observational, multicohort, retrospective analysis[J]. Lancet Respir Med, 2022, 10(4):367-377. [18] Blot PL, Chousterman BG, Santafè M, et al. Subphenotyp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treated with high-flow oxygen[J]. Crit Care, 2023, 27(1):419.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治疗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重症学组委员,四川省医学会重症医学第六届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川省老年医学会重症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及SCI论文20余篇,参编书籍4部。参与多项临床及GCP研究,作为负责人承担四川省科技厅项目3项,作为分中心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研究1项。
 后可发表评论
后可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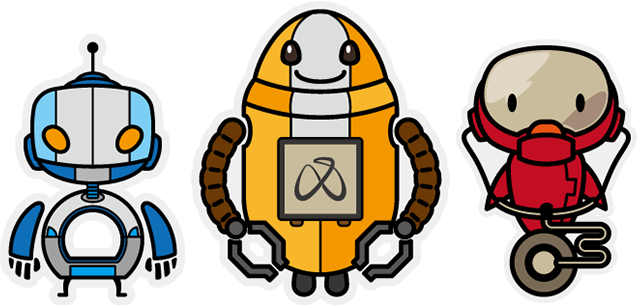
 公众号
公众号
 客服微信
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