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双林,李琦
单位: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临床中遇到的诸多疾病可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肺损伤,包括慢阻肺、哮喘等,机械通气若使用高PEEP可能都会带来通气相关的肺损伤,尤其需要关注重症COVID-19患者通气过程中可能的肺损伤。肺保护性通气是ARDS机械通气的基本策略。呼吸全过程包括外呼吸、氧转运和内呼吸。外呼吸是吸入气体在肺内经由肺泡与肺毛细血管血液进行气体交换的过程;内呼吸指的是血液输送富氧红细胞与器官组织细胞间的气体交换,细胞内的物质氧化供能过程是内呼吸。机械通气时,我们除了关注如何将气体送达患者肺内,还需关注压力、容量等因素所带来的呼吸机相关肺损伤(VILI)。近年来,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在机械通气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恰当的肺泡压能够直接影响右心前后负荷及输出量,有助于规避急性肺心病的发生。所以推而广之,肺保护性通气也会对心脏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呼吸过程中,还会存在中枢驱动的问题。对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而言,“窘迫”这一特征非常突出,这就离不开中枢驱动,而中枢驱动异常也给“肺保护”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主呼吸过强导致跨肺压增高,即患者自身呼吸造成的肺损伤(P-SILI);第二个问题是是否保留自主呼吸,如果保留,对膈肌有益,有助于规避呼吸机所致膈肌功能障碍(VIDD),但可能带来自主呼吸过强。所以,如果要实现“小潮气量”,就必须依靠其他手段。这就涉及呼吸衰竭治疗的靶点,包括内呼吸、外呼吸、体循环、肺循环以及呼吸中枢等,这其中有一些串联的因素,就是血气中的是氧、二氧化碳和pH。与pH值相关的是允许性高碳酸血症和呼吸性酸中毒,最终可能出现“酸血症”,而心脏收缩力下降、异位节律、支气管扩张剂失效,这些因素都与酸血症有一定关系。呼吸危重症常见诸多基础疾病,包括老年、结构性肺病、糖尿病、慢性肾脏病、免疫缺陷、心脏病、中毒等,ARDS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呼吸危重症的治疗原则是:呼吸支持+充分的药物治疗+并发症防治[呼吸机相关肺炎(VAP)、VILI、P-SILI]+营养免疫康复,其中呼吸支持的定位是辅助治疗。呼吸治疗的内容包括氧疗、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无创通气/有创通气、气道管理等。机械通气的目的是维持通气,满足氧合和适度通气,其中研究进展较大的是食道压/驱动压/跨肺压/EIT指导下的肺保护性机械通气、膈肌保护和右心保护。Ashbaugh和Petty等于1967在Lancet杂志发文首次提出了ARDS的概念—“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in Adults”,总结了12例具有不同病因(包括病毒性肺炎、创伤、误吸、胰腺炎、脂肪栓塞)的患者,这些患者表现出一致的临床特点,即呼吸频率快、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肺顺应性下降、双肺渗出浸润和透明膜形成,并且提出了PEEP是治疗此类常规治疗手段疗效不佳患者的有效手段。ARDS可由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引起。直接因素有:肺部感染、胃内容物大量吸入、吸入性损伤(毒气烟尘)、肺挫裂伤、肺血管炎、淹溺(海水)等,其中严重感染是首位直接高危因素,也是ARDS高病死率的主要原因。间接因素有:脓毒症、重症胰腺炎、严重创伤/烧伤、非心源性休克、药物过量、中毒、大量输血/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这些病因学和病理学因素也使得ARDS具有极大的异质性。2012年,欧洲危重病医学会(ESICM)与美国胸科学会(ATS)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ARDS的柏林定义—ARDS是一种急性弥漫性肺部炎症,可导致肺血管通透性升高,肺重量增加,参与通气的肺组织减少。其临床特征为低氧血症,双肺透光度降低,肺内分流和生理死腔增加,肺顺应性降低。ARDS急性期的病理学特征是弥漫性肺泡损伤(即水肿、炎症、透明膜或出血)。柏林定义与其他定义最核心的区别是根据氧合指数将ARDS分为轻、中、重度三种情况:轻度(200 mmHg<PaO2/FiO2≤300 mmHg), 中度(100 mmHg<PaO2/FiO2≤200 mmHg),重度(PaO2/FiO2≤100 mmHg)。2023年发布了ARDS的全球新定义,其中包括:①勿需插管,HFNC≥30 L/min或PEEP≥5 cmH2O的无创通气/连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 ②低氧血症: PaO2/FiO2≤300 mmHg或SpO2/FiO2≤315 mmHg且SpO2≤97%; ③有任一证据的双肺浸润影:CXR、CT或良好培训的超声操作员所施行的肺超声检查;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不需要PEEP、氧流量或特定的呼吸支持装置。但在临床实践中, 医疗资源、病房条件、病变性质等的差异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出现了非插管的ARDS新表型,脉搏血氧计替代、超声诊断可接受,以及将HFNC或面罩吸氧纳入了ARDS的新标准,这也使得ARDS患者群体扩大。2016年JAMA杂志发表了一项国际性、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在50个国家的ICU中,ARDS的患病率占ICU收治人数的10.4%,而且ARDS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治疗,并且与高死亡率相关;患者死因包括原发病、缺乏特效药、感染以及并发症,其中呼吸机相关并发症(VILI、VAP、P-SILI)容易被忽略。所以,肺保护性通气、膈肌保护和和右心保护在当下使用最多。
对于ARDS患者,机械通气是基础,也是“双刃剑”。机械通气的治疗作用是呼吸功能支持与替代和结构支持(胸廓和肺脏)。机械通气的损伤作用表现为气压伤(过高压力性损伤)、容积伤(过度牵张性损伤)、剪切伤(复张与萎陷交替)、P-SILI、生物伤(介质损害肺内外)、氧中毒(高浓度氧)等。导致ARDS发生VILI的易感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吸气时可扩张的肺泡数量减少,使肺泡易发生过度扩张的危险;另一个是肺泡周期性开放与塌陷所致的损伤。研究显示,予6 ml/kg的潮气量与12 ml/kg的潮气量进行机械通气比较,病死率降低了22%。VILI不仅与正压通气有关,还与基础疾病、病因、损伤程度、并发症,以及通气模式、时间、强度(压力、容量)、VIDD、右心功能障碍、自主呼吸、人机协调性和动态变化等有相关性。VILI可以分为原发损伤、代偿性损伤和医源性损伤。①原发损伤:患者出现上皮损伤、渗出浸润,可予以激素等抗炎治疗;血管内皮损伤,阻力增高,可予血浆、白蛋白、肝素治疗;②代偿性损伤:呼吸代偿驱动增强导致P-SILI;过度交感兴奋与应激;③医源性损伤:包括不恰当的液体管理、急性肺心病(ACP)、VAP等。
ARDS机械通气的目的是:纠正低氧血症,适度通气(肺保护);匹配泵衰竭、降低代谢能耗和氧需求。基于肺保护的通气策略主要包括:①适当PEEP、小潮气量、较低平台压(Pplat);②早期完全控制通气;③使用镇痛、镇静、肌松药物等;④降低驱动压和跨肺压;⑤其他措施:肺复张、俯卧位通气、高频振荡通气(HFOV)、吸入一氧化氮等;⑥ECMO和体外二氧化碳清除技术(ECCO2R)等。ARDS的早期管理是在诊断基础上按照柏林定义进行分层,基本的治疗原则是以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为基础的综合治疗。根据氧合指数设置PEEP水平,例如氧合指数很低,设置高PEEP。同时由于吸入氧浓度(FiO2)高,所以肺保护性通气又会带来氧中毒的问题。原则上尽可能将FiO2控制在60%以内,但临床中多数患者都是纯氧。这种情况下,肺保护性通气会不会因为氧的问题而失败呢?实际上,氧中毒的问题在临床上很难管理,也很难量化。基于肺保护的通气策略目的是协同增效,减少并发症。根据ARDS的严重程度,总体上予以小潮气量(6~8 ml/kg),通过P-V曲线或EIT指导,给予相对高的PEEP。另外密切观察氧合改善情况,同时保证循环稳定的基础上,调节PEEP水平。对于大多数中重度ARDS患者,俯卧位通气效果较好,时长每天尽可能在16小时以上。再结合神经肌肉阻滞剂、吸入一氧化氮、HFOV、ECCO2R、ECMO等方法。肺保护性通气是更多关注呼吸力学基础上的通气治疗,还应重视通气过程中的膈肌保护,核心是保留自主呼吸。机械通气对膈肌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研究显示:IMV 18~69 h,慢肌纤维横截面积减少57%;快肌纤维横截面积减少53%;High-PS情况下,膈肌厚度每天减少5.3%;Low-PS情况下,膈肌厚度每天减少1.5%;CMV情况下,膈肌厚度每天减少7.5%。所以,呼吸机支持过度会抑制膈肌活动,导致废用性萎缩;支持不足,导致膈肌疲劳,引起向心性损伤;而人机不同步,也会引起对抗性损伤,最终导致离心性损伤;PEEP过高,可引起膈肌初长不佳,出现纵向萎缩。所以机械通气期间要保持恰当的膈肌负荷,避免机械通气辅助过度或辅助不足。临床中可以通过跨膈压(Pdi)和膈肌超声等方法进行监测。跨膈压(Pdi)=腹内压/胃内压(Pg)-胸内压/食管内压(Pes),即Pdi=Pg-Pes。测定参数:Pdi、Pdi max,Pdi/Pdimax;要恰当设置呼吸机模式和参数,Pdi 3~12 cmH2O,以利于膈肌保护。临床中,肺保护通气策略往往会忽略肺循环。2013年发表在Intensive Care Med 杂志的一项纳入了226例ACP患者的多中心研究表明,尽管使用了保护性通气措施,ACP的发生率仍然达到22%,并且ACP组患者死亡率较高,可见右心保护策略也至关重要。肺泡萎陷/过度膨胀均会导致肺高压,引发ACP;平台压越高,ACP越高,死亡率也越高。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个体化、恰当的肺保护性通气。
总之,ARDS通气策略进入了新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采用高PEEP和潮气量,到了90年代后逐渐强调平台压,当下又强调在原来基础上加强膈肌保护和右心保护。以肺和膈肌为目标的保护性通气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肺和膈肌功能,改善患者预后。
[1] Ashbaugh DG, Bigelow DB, Petty TL, et al.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in adults[J]. Lancet, 1967, 2(7511):319-323. [2] Thompson BT, Chambers RC, Liu K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 N Engl J Med, 2017, 377(6):562-572. [3] Matthay MA, Arabi Y, Arroliga AC, et al. A New Global Definition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4, 209(1):37-47. [4] Bellani G, Laffey JG, Pham T, et al. Epidemiology, Patterns of Care, and Mortality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50 Countries[J]. JAMA, 2016, 315(8):788-800. [5] Levine S, Nguyen T, Taylor N, et al. Rapid disuse atrophy of diaphragm fibers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humans[J]. N Engl J Med, 2008, 358(13):1327-1335. [6] Jansen D, Jonkman AH, Vries HJ, et al. 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affects geometry and function of the human diaphragm[J]. J Appl Physiol (1985), 2021, 131(4):1328-1339.[7] de Vries HJ, Jonkman AH, de Grooth HJ, et al. Lung- and Diaphragm-Protective Ventilation by Titrating Inspiratory Support to Diaphragm Effort: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Crit Care Med, 2022, 50(2):192-203.
李琦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 重症医学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常委、重症医师分会和内科学分会委员,全军呼吸内科专委会副主委、感染学组组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危重症学组副组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中国老年保健研究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委,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县域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委,重庆市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委、重症医学分会副主委和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重庆市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副会长,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感染病专委会主委、重症医学专委副主委、危重症与器官功能支持专委会副主委,重庆市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执行主席;重庆英才 ·名医名师;《中华肺部疾病杂志》副主编,《中华内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等期刊编委。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主任医师,从事呼吸危重症的救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筹)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毒理学会呼吸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健康促进与教育学会复苏与生命支持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生理科学会危重病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常委,重庆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
 后可发表评论
后可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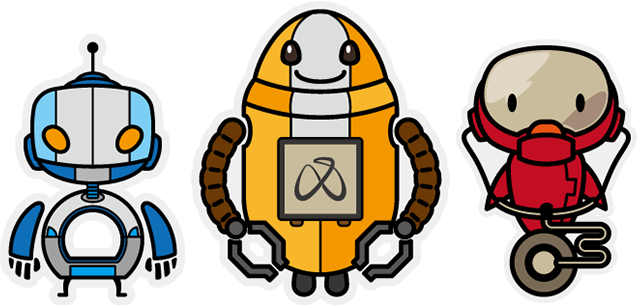
 公众号
公众号
 客服微信
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