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双林
单位: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一、人机不同步
机械通气是ICU患者常用的呼吸支持技术,在机械通气患者中经常会出现人机不同步现象。有调查显示,超过90%的机械通气患者被认为经历了某种类型的呼吸机不同步,每种类型的人机不同步都有其独特危险因素、病理生理学特征,如何识别人机不同步类型和原因也是临床医生经常会面临的挑战。常见的人机不同步有:无效触发、延迟触发、自触发和双重触发等,这些均可导致患者与呼吸机不能完全匹配。当患者的呼吸驱动力过强、过度镇静、内源性PEEP形成以及呼吸机触发灵敏度设置不恰当,都会导致无效触发。触发灵敏度设置过高、患者出现心脏震荡或呼吸机管路积水,会导致气道压力或流量变化,从而被呼吸机错误地感知为患者吸气努力,出现自主触发。而双重触发是指患者一次吸气努力会触发呼吸机连续给予两个循环的辅助通气。一般与患者有较高的呼吸驱动、短吸气设置过短有关。

但在临床救治ARDS患者过程中,我们发现患者在深度镇静和控制通气情况下,仍然有“双重触发”发生,这时患者没有主动吸气努力,意味着其没有“较强的呼吸驱动”、同时也与“短吸气时间设置过短”也没有相关性。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双触发?这里就要提到“反向触发”。

二、相关的呼吸生理学概念
在讲“反向触发”之前,我们首先了解几个呼吸生理学的概念。(1)呼吸拖带(respiratory entrainment,又名呼吸相位锁定,respiratory phase locking ),指呼吸机的机械周期及机体的神经呼吸周期之间临时性的、反复出现的固定关联。具体指在控制通气模式下,呼吸机的送气过程诱导患者的呼吸中枢发放新的或者与机械通气周期有一定程度偶联的呼吸节律。下图A为呼吸机控制通气的曲线,B为膈肌及胸骨旁的肌电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呼吸机控制通气到膈肌发送信号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每次机械通气都会偶联一个膈肌的电信号,而且这一电信号都与控制通气部分有一个时间的延迟,它不是患者主动吸气导致的机械通气,而是与呼吸机的送气过程有一定的偶联性。(2)相位差(dP)和相位角(θ):相位差指从呼吸机呼吸到神经呼吸之间的时间差,单位为秒。患者神经呼吸活动的起点被确定为食道压(Pes)突然降低或膈肌电信号(EAdi)突然升高的点。θ=dP/T tot mech×360°。相位角这一标准化的表达方式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T tot mech(呼吸机呼吸周期)和T tot neu(神经呼吸周期)之间的关系。

(3)拖带比(entrainment ratio):是指机械周期与神经周期的比例关系。1:1指1次机控通气对应1次神经呼吸,1:2指2次机控通气对应1次神经呼吸,以此类推。其中1:1是最常见也最稳定的,通常可持续较长时间,1:2则每10~12个呼吸周期容易被非拖带呼吸所打断。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呼吸机的呼吸频率设置来改善拖带特征,如从1:1改为1:3,或者完全消除拖带的存在。如下图中, A图是通过NAVA导管的EAdi监测,证实这一例压力辅助/控制模式下压力平台曲线上的小凹陷切迹,是1:1的呼吸拖带所造成。B图是通过食道压(Pes)监测,证实压力曲线上凹陷及流速曲线波形偏离预期,是1:2的呼吸拖带所造成。(4)呼吸叠加(breath stacking):患者在呼气末出现一个吸气努力,隔肌收缩,如果触发力度足够大,会导致呼吸机出现第二次送气,就会造成患者此次的吸气潮气量明显大于呼吸机设置的潮气量,称为双吸气,也即呼吸叠加,也可以是反向触发的一种形式(如下图)。有关呼吸拖带的具体机制目前仍不明确。既往在很多实验动物及早产儿等群体中都曾观察到这一现象。切断麻醉后实验动物的双侧迷走神经,呼吸拖带随即消失,提示介导黑-格反射的慢适应牵张感受器是呼吸拖带发生的关键因素,呼吸机施加的流量和压力激活了上呼吸道、肺和胸壁的牵张感受器,这些受体的反馈使呼吸中枢产生与外界刺激相匹配的相位和频率固定的自主吸气努力。然而其并非唯一因素,因为在迷走神经冷却的动物或接受肺移植的患者(迷走神经已被切断)中仍然可观察到类似现象,说明在没有来自脑干的呼吸驱动以及迷走神经支配的情况下,呼吸机送气后呼吸肌的激活可能是由其他通路介导的,如胸部或膈肌的牵张感受器或通过激活呼吸肌进行的被动的胸部运动。此外,快适应感受器、迷走C纤维连同皮质及皮质下均有一定的影响。
三、反向触发
在危重症患者机械通气过程中的呼吸拖带,最早见于Akoumianaki等于2013年发表在Chest杂志上的研究。作者描述并报告了8例接受VCV/PCV模式机械通气并且充分镇静的ARDS患者,在控制通气吸气相即将结束时,反复出现患者主动吸气做功并持续一段时间的现象。据此作者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人机交互概念—反向触发(reverse triggering),特指由呼吸机诱发的呼吸肌肉做功,用以在人机交互领域替代呼吸拖带这一概念。正常理解的触发是患者吸气做功达到触发阈值引起呼吸机给予机械通气,反向触发与此相反,呼吸机给予机械通气又诱发呼吸肌肉收缩做功,呼吸机的规律性通气周期诱发机体产生特定频率的自主呼吸,一般发生在机械周期中吸气相向呼气相转换的阶段。如下图所示,正常情况下触发是患者吸气,然后被呼吸机感知到,然后呼吸机开始送气。而反向触发是呼吸机送气,然后诱发膈肌被动收缩,患者吸气。与其他形式的呼吸机不同步一样,由于相关波形变化通常隐藏在被动呼吸中,导致反向触发诊断不足。反向触发的真实发生率尚不清楚,但有证据表明其普遍存在。一项研究发现,30%未接受神经肌肉阻滞剂治疗的ARDS患者表现出反向触发体征,而另一项研究发现100例患者中有50例存在反向触发证据。近来有学者提出反向触发的多种表型,包括早期、中期和晚期反向触发,均可能具有独特的发生率和致病因素。随着新的监测手段的出现,如膈肌电活动信号(Eadi)和食道内压,反向触发才被我们所认识。目前对反向触发的识别有通过呼吸机波形进行识别、膈肌电位监测、食道压力监测以及通过计算机算法进行识别,几种识别方法各有优缺点。
如果没有食道内压或者NAVA导管的Eadi,识别反向触发较为困难。但通过各种波形仍可能发现蛛丝马迹。如压力辅助/控制模式下吸气相压力曲线尚的负向反折,容量辅助/控制模式下压力平台期的消失,吸气/呼气流速曲线波形偏离预期,均提示可能存在反向触发。A图为VCV模式,由于反向触发开始于机械通气之后,在呼吸机进入呼气相之后仍有患者的吸气做功,阻碍了肺的弹性回缩,一方面明显降低了最大呼气流速,并使曲线轨迹不再遵循自然指数变化规律。C图为PCV模式,压力波形的平台期有小的压力降低,提示患者主动吸气做功的存在。
当患者反向触发的吸气做功幅度比较大,可能会诱发呼吸机再次重启,此时就出现双重触发。所以,很多双重触发可能是反向触发所导致。下图B和D都表现为两次吸气动作,这可能就是患者反向触发再次触发了呼吸机送气。有时反向触发和双重触发不容易区分,反向触发与双重触发产生的效果很相似,双重触发中1/3是反向触发,但两者之间的病理生理不同,可以采取5 s呼气阻断操作加以区分和识别。反向触发可通过呼气末屏气停止呼吸机送气,从而消除了诱因后无压力、流量波形的变化。而双触发在呼吸末屏气时可能诱发患者更强的吸气努力,仍可引起压力及流量波形改变。通过波形识别反向触发的优点是无创,床旁可获得。缺点是依赖于判读者经验,膈肌轻微活动时可能难以鉴别。2. 通过食道内压力(Pes)或膈肌电活动信号(Eadi)监测识别Pes和Eadi监测可以诊断反向触发,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量化反向触发期间吸气努力强度的大小。通过Pes监测识别反向触发的优点:可以量化吸气努力程度;可以进行更多呼吸力学指标的计算和监测,如跨肺压、根据压力积分计算,做功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反向触发的发生造成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情况。缺点:Pes不仅反映膈肌运动,辅助呼吸肌亦引起食道压变化,其外Pes可能受心脏震荡波的影响,且当患者的吸气努力很小时,Pes的评估可能会造成反向触发的漏诊。如下图,辅助/控制通气间隔一段时间后,患者的膈肌收缩,然后出现Pes下降,这也是机械通气控制以后诱发的膈肌收缩。

通过Eadi监测反向触发是诊断反向触发的“金标准”,当电活动出现于机控呼吸开始后可诊断为反向触发。缺点是需要食道电极管以及特殊监测记录设备,目前尚未普及,肌电水平个体差异大。如下图所示,在压力曲线峰值上有一个缺口,通过NAVA导管监测Eadi,证实这一压力辅助/控制模式下压力平台曲线上的小凹陷切迹是1: 1的反向触发所致。

通过采集包括呼吸机波形、临床指标等各种原始数据,收集处理后通过计算机处理协助加临床实时决策。Rodriguez等开发了一种计算机自动算法,能够准确检测出容量控制通气模式下ARDS患者的反向触发。但目前的研究仅采用恒流速(方波)的容量控制通气模式,对其他模式下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Pham等通过压力、流速的计算机算法和食道压法比较,计算机算法准确度为95.5%,敏感性为83.1%,特异性为99.4%,阳性预测值为97.6%,阴性预测值为95.0%。反向触发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人机不同步,因此它可产生不同的生理学效应,对患者的临床预后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容控模式下,反转触发做功会产生更高的平台压,在压力支持模式下产生更大的潮气量及跨肺压的波动,从而引起肺脏整体应力和应变的增加 。摆动呼吸现象,长时间、频繁发生反向触发可能会增加肺损伤的风险 ;但在相对同步期间发生的反向触发可以起到类似微复张的作用。在呼气阶段膈肌收缩可能也有助于维持肺的复张 。反向触发对于肺部的影响取决于反向触发呼吸努力的强度、持续时间以及肺部基础疾病情况、个体化差异等情况。触发做功会导致膈肌过负荷,造成相应肌肉组织的细胞因子释放及肌纤维的损伤,导致呼吸肌功能障碍,延长脱机时间。另一方面,反向触发可以保留在被动通气时的膈肌活动,从而防止呼吸肌肉的废用性萎缩。对于呼吸肌功能的影响取决于反向触发的强度在废用性萎缩和负荷性损伤之间的平衡。反向触发增加了胸腔内负压,引起右心室前负荷和左心室后负荷的增加,这两者都可能导致心力衰竭。反向触发的呼吸努力可增加呼吸肌做功和氧耗,甚至导致分钟通气量以及二氧化碳分压的升高。研究发现,有反向触发的患者比没有反向触发的患者可能更有能力触发呼吸机,甚至在第2天拔管 。反向触发对ARDS可能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其发生率或潜在的预测因素目前仍不清楚。研究表明,在ARDS患者中,反向触发与机械通气时间长短无关,但与90天住院病死率的降低独立相关 。由于反向触发的产生机制尚不明确,对反向触发的处理尚无确切措施,但通过目前较多的研究发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处理。 增加镇痛和镇静剂的镇静深度是患者-呼吸机不同步的管理策略。它通过抑制患者的呼吸驱动,有效降低了某些形式的不同步的发生率。但多项研究证实,反向触发发生率可能随着镇静深度的增加而增加。最近的文献无法显示镇静剂给药与反向触发发生率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一些研究表明,通过使用阿片类药物改善了异步性指数。尽管有一些相互矛盾的报告,但专家意见支持深度镇静作为反向触发的风险因素。总的来说,在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之前,应尝试减少镇静和镇痛作为对抗反向触发的潜在手段。神经肌肉阻滞剂(NMBA)可能对经历呼吸机不同步和高跨肺压波动的患者有益,并且可有效终止反向触发 。在2019年时,有学者又重复了这样的试验,观察了两组患者,一组患者使用了肌松药,另一组患者给予了深镇静。研究者发现,在使用肌松药的患者中没有出现反向触发。而对照组没有使用肌松药,在维持深镇静的患者中,10例中有3例(33%)出现了反向触发。可以看到,反向触发在那些深镇静但没有使用肌松药的患者中确实存在。在ARDS早期阶段,使用NMBA可能是优先的选择。必须权衡 NMBA的益处与其显著的不良反应特征,包括机械通气期间膈肌功能障碍的恶化,结合这些患者所需的更深度的镇静水平,还可能导致更长时间的机械通气。优化呼吸机设置是管理反向触发的中心策略。虽然关于调整呼吸机策略以解决反向触发的数据仅限于回顾性研究和病例报告,但将呼吸机设置管理为其他类型不同步干预的有力证据支持这种干预途径。①改变潮气量或压力:研究表明急性呼吸衰竭患者1/3的呼吸叠加与反向触发有关,同时也证实了反向触发与低潮气量独立相关。②降低或增加指令频率:增加呼吸机频率,或者更常见的是降低呼吸机频率,直到所有呼吸都由患者努力启动,这可能是消除反向触发的有效策略。因此,呼吸频率对反向触发的影响可能不在于次数的增加或减少,而在于控制频率是否接近患者的中枢自主频率。③降低触发灵敏度:虽然降低呼吸机的触发灵敏度可以有效减少反向触发相关的双重触发,但它不能消除潜在的呼吸肌收缩或负胸腔内压的有害影响。

四、小结
反向触发是一种我们尚未充分认识的人机不同步类型,可以通过Pes或Eadi监测和识别。此外,呼吸机的各种波形对识别反向触发也有一定的提示作用。反向触发有益也有害,可以通过减少镇静和镇痛、使用肌松药物及改变呼吸机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反向触发。
[1] Akoumianaki E, Lyazidi A, Rey N, et 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induced reverse-triggered breaths: a frequently unrecognized form of neuromechanical coupling[J]. Chest, 2013, 143(4):927-938.
[2] Rodriguez P O, Tiribelli N, Fredes S, et al. Prevalence of Reverse Triggering in Early ARDS: Results From a Multicenter Observational Study[J]. Chest, 2021, 159(1):186-195.
[3] Bourenne J, Guervilly C, Mechati M, et al. Variability of reverse triggering in deeply sedated ARDS patients[J]. Intensive Care Med, 2019, 45:725-726.
[4] 张春艳, 夏金根, 陶程, 等. 机械通气患者反向触发研究进展[J].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2, 21(4): 297-301.
[5] Pham T, Montanya J, Telias I, et al. Automated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reverse triggering effort under mechanical ventilation[J]. Crit Care, 2021, 25(1):60.
[6] Murray B, Sikora A, Mock JR, et al. Reverse Triggering: An Introduction to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harmacologic Implications[J]. Front Pharmacol, 2022, 13:879011.

-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主任医师
-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筹)委员
-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治疗与肺康复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分会常委
- 重庆健康促进与教育学会复苏与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重庆市生理科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重庆市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基层呼吸工作委员会委员
- 重庆市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呼吸危重症与呼吸治疗工作组副组长
*本文根据“呼吸危重症菁英秀”第二十二期专题视频整理,感谢刘双林教授予以审核。

 后可发表评论
后可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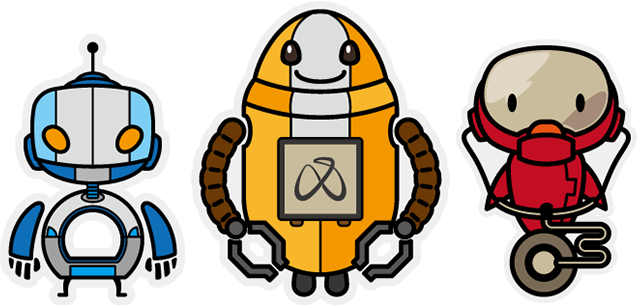
 公众号
公众号
 客服微信
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