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妍,刘纯,李颖
患者,男性,22岁,主诉:头昏、发现血象异常1天。入院时间:2022年7月27日。
患者2022年7月26日头昏、血常规发现白细胞异常增高,无发热,无咳嗽咳痰,稍感腹胀,无明显腹痛腹泻,无鼻出血、牙龈出血,无血尿黑便。我院骨髓穿刺检查提示"急性髓系白血病",收入血液内科。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等均无特殊。
体温36.8℃,脉搏84次/分,呼吸20次/分,血压108/50 mmHg,贫血貌,全身可见散在出血点,浅表淋巴结未扪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心律齐,无杂音。腹部平坦,全腹无压痛以及反跳痛,肝脾未扪及,Murphy征阴性,移动浊音阳性,肠鸣音正常约4次/分,双下肢无水肿。
- 血常规:白细胞26.57×109/L,血红蛋白61 g/L,血小板32×109/L。
- 肝肾功能:白蛋白35 g/L,尿酸464 μmol/L。
- 心肌酶、肌钙蛋白、脑利尿钠肽、电解质、淀粉酶、凝血常规、大便常规未见明显异常。
- 骨髓细胞形态:急性髓系白血病M2a型;流式细胞学:骨髓检测77.63%(占有核细胞)的细胞考虑为异常原始髓系细胞来源(M2可能);融合基因检测WT1阳性,二代测序:CEBPA双突变、CBL突变、CSF3R突变;染色体46(XY)。
2022年7月30日开始行标准IA方案:伊达比星15 mg 第1天,20 mg第2~3天;阿糖胞苷170 mg第1~7天。病情折点:8月7日,患者体温升高38℃,血液内科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 g 静脉滴注q8h抗感染治疗。后患者持续发热且伴有右下腹痛,无反跳痛,肛门有排气排便。复查血常规:白细胞0.3×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0×109/L(↓),血红蛋白64 g/L(↓),血小板8×109/L(↓)。降钙素原0.267 ng/ml;全血培养:无厌氧菌、细菌、真菌生长。腹部彩超示:38 mm×2 mm混合回声包块,右下腹肠管壁增厚,考虑为炎性包块。8月10日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升级为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替加环素抗感染治疗。8月12日,发热加重,体温最高达到39.5℃,仍诉右下腹痛,未排气排便。加用卡泊芬净抗真菌治疗。8月14日,患者体温最高38℃,右下腹痛,未排气排便;复查腹部彩超: 右下腹可见一大小106 mm×36 mm混合回声包块, 考虑为炎性包块, 较前明显增大。将替加环素改为利奈唑胺。8月16日,体温无好转,全腹胀痛伴右下腹绞痛;查体:腹部叩诊呈鼓音,右下腹压痛、反跳痛,肠鸣音消失。新增诊断:腹腔感染,考虑:麻痹性肠梗阻?梗阻性肠梗阻?脓毒血症?复查腹部CT:①升结肠、回盲部及回肠末端、阑尾肠壁增厚,并低位小肠梗阻,性质待定,考虑炎症所致可能,局部肠缺血?②腹膜炎,腹水较前减少,右侧腹部皮下水肿(图1)。8月17日,血氧饱和度下降,神志呈嗜睡状态,转内科ICU,行胃镜下肠梗阻导管置管。继续抗感染治疗方案:卡泊芬净+亚胺培南+利奈唑胺。患者体温38~39℃。复查血常规:白细胞0.2×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0.01×109/L(↓);全血培养:无厌氧菌、真菌、细菌生长;GM试验0.301 μg/L;G试验<10 pg/ml;降钙素原1.3 ng/ml(↑)。8月20日,患者体温36℃,腹胀腹痛无明显好转,右下腹局部皮肤呈黑褐色且有破溃表现(图2)。复查腹部CT:右下腹皮肤破溃膨出,较前进展(图3)。


患者局部皮肤呈黑褐色,结合患者白血病+化疗治疗基础,考虑毛霉感染可能,停卡泊芬净改两性霉素B粉针。组织MDT讨论。
第一次MDT(8月21日):血液科、感染科、消化科、普外科、麻醉科、营养科、临床药学科。
MDT意见考虑:低位小肠梗阻,麻痹性肠梗阻,腹膜炎;暂无手术条件,积极寻找病原学及药敏结果,调整抗感染方案;鼻胆管前端球囊抽出5ml,减轻对肠壁等压迫;腹腔穿刺引流,减少腹水,监测腹压;鼻饲石蜡油,盐水低张性灌肠;外科手术作为最后手段。
8月21日, 患者体温36℃, 腹胀腹痛未好转。利奈唑胺疗效不佳, 因不能排除阳性球菌的血流感染, 停用利奈唑胺, 改为达托霉素抗感染治疗。血常规:白细胞8.32×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7.86×109/L。降钙素原6.19 ng/ml(↑)。皮肤破溃处穿刺液培养无细菌、真菌生长。全血培养无厌氧菌、细菌、真菌生长。留取皮肤病变组织完善病原学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传统方法(培养、免疫与PCR)循证依据多,应用广泛, 成本低, 可以直观看到药敏结果, 方便选药, 但阳性率低、耗时耗力,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分子诊断方法快速, 敏感性高, 但成本相对较高(图4)。
图4 传统方法与分析诊断方法比较
临床病原学诊断已进入mNGS检测时代。目前临床常用微生物检验的“五朵金花”——显微镜直接镜检、分离培养与鉴定、免疫学检测和生物标记、分子生物学技术、质谱鉴定技术。其中mNGS具有明显的优势:无需预设,无需培养,无偏倚;直接提取临床样本中的DNA/RNA,进行高通量测序;经过专用病原数据库比对,以及生信分析,一次性完成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病原体的检测。
本例患者皮肤组织mNGS检出真菌:总状毛霉(序列数696),枝孢样枝孢霉(序列数523),小孢根霉(序列数465)。细菌、DNA病毒、寄生虫均未检出。未检出RNA病毒。毛霉病可表现为皮肤、鼻-眼眶-中枢、肺部/呼吸道感染累及多个器官。如图5所示:A为伤口/皮肤感染,图示为车祸后由鳞质霉属所致左腿广泛的皮肤毛霉病;B为鼻-眼眶-颅内感染(ROCM),图示为不同患者出现的ROCM症状,B1为血液肿瘤患者化疗后出现的鼻部和皮肤坏死;B2为糖尿病患者因眼眶感染导致的水肿;B3-4为糖尿病患者MRI下出现的由鼻腔-眼部延伸至颅内的感染病灶;B5为出现鼻部症状患者出现口腔内霉菌感染;C为肺部/下呼吸道感染,图示为罹患肺部毛霉感染患者的CT影像学表现,表现为磨玻璃影周围环绕实变影;D为消化道感染,左侧上下图片所示为罹患上消化道霉菌病患者在接受内镜检查中发现的消化道穿孔病灶,以及CT下影像学表现;右图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接受化疗后出现的腹部囊肿。 图5 侵袭性毛霉感染
欧洲医学真菌学联盟(ECMM)推荐的毛霉病诊断流程如图6所示。
图6 ECMM推荐的毛霉病诊断流程
通过抗真菌药物抗菌谱(表1)可以发现,艾沙康唑和泊沙康唑能够同时覆盖曲霉和毛霉,两性霉素B对土曲霉无效对毛霉有效,伏立康唑和卡泊芬净对毛霉无效。
表1 抗真菌药物抗菌谱

8月25日停用达托霉素,由于当时艾沙康唑暂时不可及,所以使用了两性霉素B胆固醇硫酸酯250 mg/d+亚胺培南抗感染。8月29日腹部MRI平扫+增强+弥散加权成像(DWI):右侧中下腹腔内(以右半结肠为中心)邻近前腹壁-腹膜后巨大边缘环形强化病灶,范围较前稍进展(图7),考虑升结肠缺血坏死,感染较前稍进展,并肠瘘可能。图7 腹部MRI平扫+增强+DWI(2022-08-29)第二次MDT(8月29日):血液科、感染科、普外科、消化科、麻醉科、营养科、临床药学科。MDT意见:患者目前有手术指征,但手术风险极高,预后极差,且费用高昂,继续积极抗感染治疗。患者体温36℃,腹胀腹痛较前稍缓解,可解少量大便,肠梗阻解除,生命体征平稳,转回血液科继续治疗。抗感染: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两性霉素B胆固醇硫酸酯+艾沙康唑200 mg q8h(第3天开始200 mg qd)。9月2日, 患者体温36.7℃, 全腹胀痛好转, 右下腹皮肤溃烂黑痂, 范围约7 cm×8 cm, 局部破溃渗液(图8)。9月4日晚患者再次出现发热,体温38.3,将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改为亚胺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查血常规:白细胞13.12×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11.43×109/L;降钙素原3.57 ng/ml。分泌物细菌(真菌)培养: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9月5日腹部MRI平扫+增强+DWI: 右侧中下腹腔内(以右半结肠为中心)-邻近前腹壁-腹膜后巨大边缘环形强化病灶较前向外膨出、范围较前缩小(图9),考虑升结肠-邻近小肠及腹壁缺血坏死并感染, 肠瘘形成可能, 肠梗阻较前改善。图9 腹部MRI平扫+增强+DWI(2022-09-05)9月9日患者右下腹坏死物膨出,边缘进一步破溃,脱落,暴露腹腔内容物(图10)。在2019年ECMM发布的《毛霉病诊断和管理全球指南》中,指南小组强烈支持,除全身抗真菌治疗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早完成毛霉病的外科治疗。如有需要,应反复行切除或清创术。第三次MDT(9月9日):感染科、普外科、麻醉科、营养科、消化科、烧伤科、ICU、康复科。MDT意见考虑:患者有手术指征,但手术风险极高,需要多学科联合手术同时进行;尽快完善全腹部CT+腹部血管CTA,完善术前高风险谈话及手术/麻醉评估,患者及家属手术意愿强烈可考虑充分术前准备后手术。9月9日腹部CT+腹部血管CTA:肝中动脉瘤;腹主动脉+肠系膜上、下动脉+肾动脉CTA未见异常。9月10日行腹壁坏死组织切除+回肠部分切除+回肠造瘘+肠粘连松解术,术后转ICU观察。术中见:右下腹一13 cm×13 cm坏死腹壁与肠管组织,与周围组织无粘连,予以取出,回盲部、部分乙状结肠、右侧上段输尿管包裹在腹壁坏死组织中(图11)。病理组织活检:骨骼肌及肠壁可见大量真菌菌丝、孢子及细菌菌团,且部分真菌菌丝及孢子似位于脉管内,倾向侵袭性真菌病并广泛播散;见阑尾组织显著急性坏疽性阑尾炎,阑尾管壁及管腔内见真菌菌丝及孢子。9月14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发热,为求坏死腹壁修复,转入烧伤科继续治疗。9月15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胆仍有腹痛、腹胀,转入胃肠外科治疗,后续进食半流质,腹痛缓解,造瘘处有排便排气。术后持续予以两性霉素B胆固醇硫酸酯+艾沙康唑治疗。9月20日腹部增强CT示(图12):“腹壁坏死组织切除+回肠部分切除+回肠造瘘+肠粘连松解术”术后改变,右中下腹术区少量渗出、积液;左侧回肠造瘘口近端小肠积液、积气扩张;右侧输尿管上段继发右肾及输尿管上端轻度积水同前;盆腹腔脓肿较前吸收。肠腔内高密度影,造影剂残留?肝中动脉动脉瘤较前增大。肝脏多发低密度灶同前,仍考虑小脓肿形成可能。9月22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复查骨髓形态及流式均未见异常细胞。11月1日,烧伤整形科于全麻下行"右腹壁腹膜补片修补+腹壁缺损右股前外侧皮瓣转移修复术"。术前已停用两性霉素B,予以艾沙康唑口服维持治疗。2024年1月3日随访腹部CT提示患者恢复较好(图13)。
图13 随访腹部增强CT(2024-01-03)
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对2000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发表的毛霉病病例进行分析,来自600篇文献报道的851例患者总体死亡率接近50%(血液肿瘤伴随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者在另一文献中对患者的治疗和临床预后进行进一步分析,肺部感染和累及中枢系统伴随极高的死亡率,约为70%。另有研究表明约有半数毛霉病患者死亡,免疫抑制增加毛霉病的死亡风险。我国学者孙军平等研究发现,肺是毛霉常见的感染部位,其他如皮肤、中枢神经系统、眼、胃肠道等部位感染也不容小觑,其中胃肠道感染病死率高达52.2%。
毛霉病的全因死亡率在40%~80%之间,其死亡率取决于基础条件和感染部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大面积烧伤的患者预后最差。弥散性疾病,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死亡率往往高于80%。生存率的提高与早期诊断和应用包括积极的外科清创术在内的多学科治疗方法有关。
对于早期真菌感染,预防尤为重要;粒缺且发热是其高危因素,对于早期鉴别至关重要;霉菌感染多变,毛霉引起皮肤发黑应引起重视。传统病原学诊断方法和mNGS检测的碰撞与结合,能够为真菌感染提供重要线索。真菌肺炎的治疗,关键是抗真菌药物的应用,应该合理精准地选药,使用疗程不固定,需要数周到数月的治疗。免疫缺陷得到解决,例如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得到解决,免疫抑制可以逐渐减弱或停止,可以继续治疗直至症状和体征缓解,感染控制,影像学明显改善。MDT是一种先进的诊疗模式,它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提高了诊疗质量,降低了患者死亡率,在疑难复杂疾病诊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患者救治成功离不开多学科团队的积极努力和密切合作以及家属的全力支持。
[1] 高晓东,刘思远,钟秀玲,等. 跌宕奋进30年中国感染控制1986-2016[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2] 王辉.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3] Cornely OA, Alastruey-Izquierdo A, Arenz D, et al. Global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mucormycosis: an initiative of the 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Medical Mycolog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Mycoses Study Group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nsortium.[J]. Lancet Infect Dis, 2019, 19(12):e405-e421.[4] Bhansali A, Bhadada S, Sharma A, et al. Presentation and outcome of rhino-orbital-cerebral mucormycosi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J]. Postgrad Med J, 2004, 80(949):670-674.[5] Huang H, Xie L, Zheng Z, et al. Mucormycosis-induce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ulcer perforation i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 a report of two cases[M]. BMC Gastroenterol, 2021, 21(1):311.[6] Gallo F, Vija L, Le Grand S, et al. Diagnosis of an intestinal mucormycosis 'fungus ball' located with PET/CT with [18F] FDG-PET/CT[J]. Eur J Hybrid Imaging, 2019, 3(1):21. [7] Patterson TF, Thompson GR 3rd, Denning DW, et 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spergillosis: 2016 Update by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J]. Clin Infect Dis, 2016, 63(4):e1-e60. [8] Koehler P, Bassetti M, Kochanek M, et al. Intensive care management of influenza-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J].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9, 25(12):1501-1509.[9] Goyal J, Fernandes M, Shah SG. Intracameral voriconazole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fungal endophthalmitis resulting from keratitis[J]. Am J Ophthalmol, 2010, 150(6):939; author reply 939-40. [10] DeLone DR, Goldstein RA, Petermann G, et al. Disseminated aspergillosis involving the brain: distribution and imaging characteristics[J]. AJNR Am J Neuroradiol, 1999, 20(9):1597-1604.[11] Studemeister A, Stevens DA. Aspergillus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in immunocompetent hosts: role of triazole antifungal therapy[J]. Clin Infect Dis, 2011, ;52(1):e1-e6. [12] Nivoix Y, Ledoux MP, Herbrecht R. Antifungal Therapy: New and Evolving Therapies[J]. Semin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0, 41(1):158-174. [13] Jeong W, Keighley C, Wolfe R, et al. The epidemiology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mucormyc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ase reports[J].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9, 25(1):26-34. [14] Steinbach WJ, Marr KA, Anaissie EJ, et al. Clinical epidemiology of 960 patients with invasive aspergillosis from the PATH Alliance registry[J]. J Infect, 2012, 65(5):453-464. [15] Nicolle MC, Bénet T, Thiebaut A, et al. Invasive aspergillosis in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incidence and description of 127 cases enrolled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prospective survey from 2004 to 2009[J]. Haematologica, 2011, 96(11):1685-1691.[16] Corcione S, Lupia T, Raviolo S, et al. Putative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within medical wards and intensive care units: a 4-year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ingle-centre study[J]. Intern Emerg Med, 2021, 16(6):1619-1627. [17] Sun KS, Tsai CF, Chen SC, et al. Clinical outcome and progno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n 11-year follow-up report from Taiwan[J]. PLoS One, 2017, 12(10):e0186422.[18] Jeong W, Keighley C, Wolfe R, et al.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mucormyc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ase reports[J].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19, 53(5):589-597.[19] 孙军平, 汪建新, 张明月, 等. 1980-2020年我国报告的310例毛霉菌病病例分析[J]. 国际呼吸杂志, 2022, 42(4):279-284. 
湘雅三医院呼吸科 副主任医师,内科学博士;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院访问学者;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中青年医师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呼吸肿瘤协作组湖南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第八届结核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华南区呼吸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呼吸科专业组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第一届肿瘤免疫与靶向治疗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第一届呼吸肿瘤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医患沟通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肿瘤研究与转化分会委员,湖南多学科协作肺癌诊治联盟委员,湖南省肺癌早诊联盟委员,湖南省住院医师级全科师资培训专家。

刘纯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呼吸ICU亚专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健康科技促进会气道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呼吸病学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呼吸慢病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呼吸病学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会委员,全国新冠抗疫先进个人。

李颖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血液学博士;湖南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诊断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血液分会第一届副主任青年委员,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临床医学教育研究会诊断学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血液健康分会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白血病分会会员。
 后可发表评论
后可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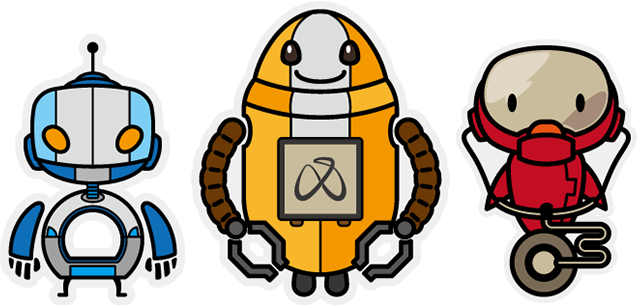
 公众号
公众号
 客服微信
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