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方式
方式一:
PC端网页:www.rccrc.cn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可将此网址收藏并保存密码方便下次登录
方式二:
手机端网页:www.rccrc.cn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可将此网址添加至手机桌面并保存密码方便下次登录
方式三:
【重症肺言】微信公众号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注:账号具有唯一性,即同一个账号不能在两个地方同时登录。
作者:赵世龙,邢丽华
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三科
【摘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呼吸危重症患者病情最严重情况中的一种。ARDS患者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过程中的镇痛镇静策略尚未有统一的规范。个体化管理策略可能是未来的方向,药物的选择及应用要考虑ECMO的药代动力学、药物的理化性质和患者自身的因素。治疗过程中的镇静深度应根据治疗进展不断做出调整,治疗早期往往会给予深度镇静,随着治疗的进展,可逐渐减少镇静剂的用量,恢复自主呼吸。
1. ECMO的药代动力学
2. 患者相关因素
3. 镇痛药物
4. 镇静药物
5. 吸入性镇静药物
⭐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 中国成人ICU镇痛和镇静治疗指南[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8, 30(6):497-514.
[2] Bellani G, Laffey J G, Pham T, et al. Epidemiology, Patterns of Care, and Mortality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50 Countries[J]. JAMA, 2016, 315(8):788-800.
[3] Cheng V, Abdul-Aziz M H, Roberts J A, et al. Optimising drug dosing in patients receiving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J Thorac Dis, 2018, 10(Suppl 5):S629-S641.
[4] Lemaitre F, Hasni N, Leprince P, et al. Propofol, midazolam, vancomycin and cyclosporine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in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circuits primed with whole human blood[J]. Crit Care, 2015, 19:40.
[5] Shekar K, Roberts J A, Mcdonald C I, et al. Sequestration of drugs in the circuit may lead to therapeutic failure during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Crit Care, 2012, 16(5):R194.
[6] Wagner D, Pasko D, Phillips K, et al. In vitro clearance of dexmedetomidine in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Perfusion, 2013, 28(1):40-46.
[7] Chanques G, Constantin J M, Devlin J W, et al. Analgesia and sedation in patients with ARDS[J]. Intensive Care Med, 2020, 46(12):2342-2356.
[8] Bakdach D, Akkari A, Gazwi K, et al. Propofol Safety in Anticoagulated and Nonanticoagulated Patients During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ASAIO J, 2021, 67(2):201-207.
[9] Hohlfelder B, Szumita P M, Lagambina S, et al. Safety of Propofol for Oxygenator Exchange in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ASAIO J, 2017, 63(2):179-184.
[10] Lamm W, Nagler B, Hermann A, et al. Propofol-based sedation does not negatively influence oxygenator running time compared to midazolam in patients with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Int J Artif Organs, 2019, 42(5):233-240.
[11] Pandharipande P P, Pun B T, Herr D L, et al. Effect of sedation with dexmedetomidine vs lorazepam on acute brain dysfunction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the MEN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 2007, 298(22):2644-2653.
[12] Mesnil M, Capdevila X, Bringuier S, et al. Long-term sedation in intensive care unit: a randomized comparison between inhaled sevoflurane and intravenous propofol or midazolam[J]. Intensive Care Med, 2011, 37(6):933-941.
[13] Grasselli G, Giani M, Scaravilli V, et al. Volatile Sedation for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Patients on Veno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and Ultraprotective Ventilation[J]. Crit Care Explor, 2021, 3(1):e0310.
[14] 李晖, 黄青青. 镇痛镇静评估方法的局限与进步[J].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网络版), 2017, 3(4):258-261.
[15] Dzierba A L, Abrams D, Madahar P, et al. Current practice and perceptions regarding pain, agitation and delirium management in patients receiving veno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J Crit Care, 2019, 53:98-106.
[16] Shehabi Y, Chan L, Kadiman S, et al. Sedation depth and long-term mortality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critically ill adults: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multicentre cohort study[J]. Intensive Care Med, 2013, 39(5):910-918.
[17] de Backer J, Tamberg E, Munshi L, et al. Sedation Practice in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Treated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 Retrospective Study[J]. ASAIO J, 2018, 64(4):544-551.
[18] Papazian L, Aubron C, Brochard L, et al. Formal guidelines: management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 Ann Intensive Care, 2019, 9(1):69.
[19] Guérin C, Beuret P, Constantin J M, et al. A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observational prevalence study on prone positioning of ARDS patients: the APRONET (ARDS Prone Position Network) study[J]. Intensive Care Med, 2018, 44(1):22-37.
[20] Yu X, Gu S, Li M, et al. Awake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for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hich Clinical Issu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J]. Front Med (Lausanne), 2021, 8:682526.
[21] Yeo H J, Cho W H, Kim D. Awake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ostoperativ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 J Thorac Dis, 2016, 8(1):37-42.
⭐ 作者介绍
邢丽华
赵世龙
 后可发表评论
后可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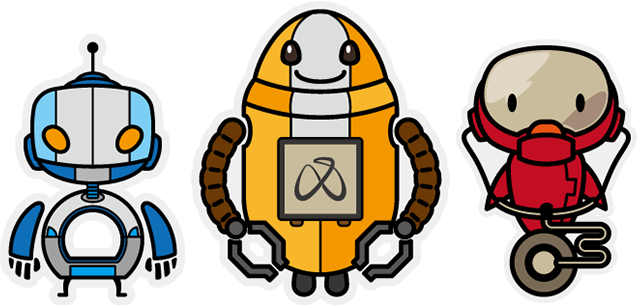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公众号
公众号
 客服微信
客服微信